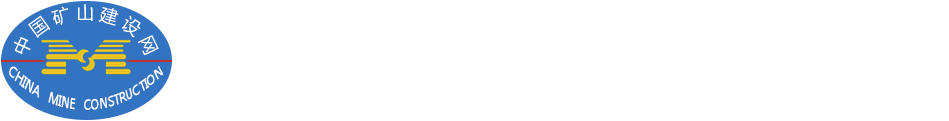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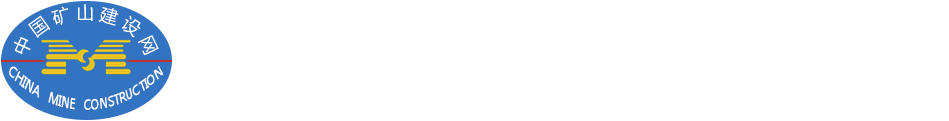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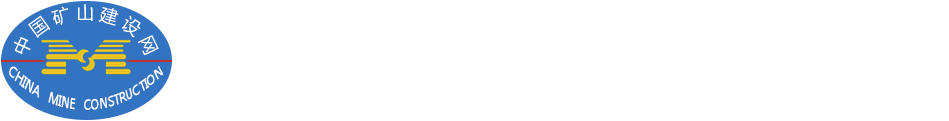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唐文方,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分别获法学学士学位和政治学博士学位,曾就职于匹兹堡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斯坦佛大学,现任美国爱荷华大学政治学与国际问题研究斯坦利华夏讲座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教授。
原题
1.专业培养
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1977年第一批考进北大国际政治系的,即现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前身,我想去国政系,主要是想学外语,对国际政治的了解,是很多年之后的事了。
在美国,国际政治包括两层意思: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一般是设在政治学这个更大的学科之下,政治学在美国历来是社会科学中的大系,但是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取消了政治学,理由是政治就是马克思主义,其它没有必要讨论,直到1990年代末,政治学才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在1960年代,中国意识到对外交往和对外国了解的重要性,据说由周恩来提议,在北大、人大和复旦组建了3个国际政治系,那时的分工是:复旦研究欧美、人大专攻苏联东欧,北大负责第三世界。
我们的课程基础课主要是中共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还有英文,专业课主要是国际关系史、国际法、世界经济、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例如拉丁美州革命运动、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和非洲民族独立运动。
当时上课的有讲党史的石志夫老师,版书写的非常漂亮,讲国际共运史的张汉清老师和宁骚老师,讲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梁守德老师和潘国华老师,讲拉美民运的女老师王杰,漂亮又有风度,讲中东政治的李湖老师,还有讲帝国主义论的王炳元老师,我们的班主任是研究东南亚的张锡镇老师,系主任是中国著名的老一辈政治学家赵宝煦老师,党总支书记是后来任海淀区委书记和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的沈仁道老师,还有著名社会学家雷洁琼也在我们系任职,不过我们很少见到她。
我们的英文老师叫孟庆友,教学很认真负责,对学生也很好,他的专长是英文的介词,如at, in, of, to等等,这些词虽然看起来简单,但是用对了还真不容易,从孟老师那里学到的英文介词的用法,至今还记得,对我后来出国英语水平的提高很有用。
我们那时候很少有英文外教,记得快毕业时终于有了一个外教,好像是哈佛大学的一个交换生,他给我们上课就是用英语闲聊天,记得他说他非常喜欢硬壳虫乐队,他还声称为了看硬壳虫乐队的演出,把他妈卖了都行,他说这话时表情非常严肃,我至今也不清楚他是认真的还是在开玩笑,因为那时候不知道从哪里得出的印象,美国人的家庭关系都很松散,把妈卖了说不定真能做得出来。
那时候老师讲课有一套固有的方法,首先强调的是把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理清楚,考察每个事件或人物的历史背景、事件产生的原因,以及事件的意义和后果,一般要至少分析出两三条,上课要记很多笔记,考试要死记硬背很多笔记上的内容,刚开始两年还比较认真,后来就觉得本系老师的知识结构和教学方法已经过时了,总是抱怨这种学习方法太死板,没有给学生足够的空间去思考,于是经常不上课,整天整夜地打桥牌,考试时借其他同学的笔记看一看、背一背就行了。
好在北大的传统是从来不计考勤,不来上课没关系,只要考试能过就行,直到后来出国继续学习才发现,北大的本科教育其实是培养了在学术界生存的一些最基本最有用的技能。
那时打桥牌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牌友除了同班同学杨建和丁建,还有78级的仲伟学,老仲家在东北的林场,那时候已经有4个孩子,家里生活比较困难,但他学习很刻苦,上课笔记做的很好,我后来总结出,只要借老仲的笔记,就可以完全不用上课,成绩也会考的不错,为此我始终很感激他,可惜听说他毕业后回到东北不幸患癌症去世了。
此外,在北大念书时,对自己所学专业的用处也认识甚浅,当时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国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赶超欧美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的革命与政变的关注像对马列主义的关注一样越来越少,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印度尼西亚亲中亲共的总统苏加诺倒台的原因,写完之后就再也没有看过它,直到30年后有机会到东南亚访问,才意识到我们所学专业的真正意义所在。
2.老三届
那时候我们国政系77级有31个同学,因为是文革后的第一届高考,班里不乏老三届的学生,其中有王缉思、黄晴、李援朝、赵全胜等等。
王缉思是我们班学习最好的,他上学报到晚了,听说是从三门峡水电站来的电工,还背着一个正宗的电工包。缉思一脸的福相,胖乎乎的,咋一看朴实得不能再朴实了,说起话来总是在微笑,平时看起来性格稳重,但班级间篮球比赛时却生龙活虎,有些像拼命三郎。
缉思在我们班英文考试成绩总是第一名,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在北大的学术气氛中长大的,他爸是中国当时非常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那时每当英文考试的时候我都会暗中和缉思较劲,总想考过他,无奈他总是考全班第一,后来有一次我终于考的分数比他高,但是因为他出了意外。
那次是上体育课,老师要求我和另一个同学潘淇手拉手,让缉思在我俩的胳膊上翻360度的跟斗,不料他翻了一半我们没兜住,头冲下戳到了地上,当时磕的不轻,赶快上校医院,诊断是轻微脑震荡,头疼的无法准备第二天的英语考试,那次考试是我唯一分数超过他的一次,但至今心里还很内疚,缉思,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很喜欢和缉思聊天,他说起话来常常出人意料。例如一次他对我说,他当老师后,学生曾经问过他,学习党史和共运史以后会有什么用?他想了半天,对学生说,是没什么用呀。我以为他会去教导学生,他却能从学生的角度来看问题,然后去诱导他们。缉思毕业后在社科院美国所当了多年的所长,后来又回北大作了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他做学问非常扎实,是中国数一数二的研究中美关系的顶尖学者,他写的关于国际关系的文章,深受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重视,是他们的必读之物。
赵全胜是我们班的支部书记,他很善于做同学的思想工作,和他聊天总有一种安全感,那时侯他经常和他以前在北京101中的同学、北大历史系77级的BXL一起在学五食堂吃晚饭,有时候也会叫上我,我们每次吃饭都会山南海北地聊得兴高采烈,BXL给我的印象是性格外向、待人友善、有人格魅力,后来他考上了社科院新闻所的研究生。
老赵是我们班第一个出国留学的,他1981年就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斯卡罗宾诺手下读博士,后来成了研究中美日关系的著名学者,常常在美国国会出席听证会,现在任教于美利坚大学。
黄晴是班里的另一位老大哥,他是个不拘小节的人,上学报道时把户口本丢了都不知道,直到有人捡到送回来。老黄为人极为谦虚,说话的口气从来都不是命令式的或下结论式的,总是用一个问号结尾,给人的感觉他总是在征求别人的意见,以示对对方的尊重,后来上中共党史课才知道,老黄的父亲黄克诚是中共党史的著名人物,1950年代就当了总参谋长和中央军委秘书长,1959年随彭德怀的倒台而受牵连,一直不顺,每次石志夫老师在党史课上讲到彭德怀和黄克诚反党集团时,都是小心翼翼地绕着讲的。可能从小因为父亲挨整,老黄为人处事非常低调。
后来老黄和BXL一样,从北大考上了社科院新闻所的研究生,在人民日报做记者,后来做了人民日报国际部的主任,经常能看到他写的评论文章,他的文章很像他的为人,低调、不夸张,但逻辑性非常强,有理、有力、有节。后来才知道,老黄娶的妻子是北大游泳队的一位女生,当时我也在游泳队,记得她好像是物理系的,人很出众,性格也很随和。
李援朝是我们班里的另一个老大哥,他爸也是中共党史的著名人物,也是上党史课时才发现的,叫李卓然,1920年代就去法国勤工俭学,1930年代初就是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比老黄的父亲资格更老,石志夫老师讲党史讲到这一段时还经常和李援朝核对事实。那时我和援朝睡上下铺,他睡上面,我睡下面。他把我当做小兄弟,对我很照顾,经常给我指点学习的方法,有时还会和我一起策划中国未来的外交政策,周末还让我到他家去。他家住在东四的一个很大的四合院里,一进门还有影贝。
援朝是当时我们班为数不多的已经结了婚的学生之一,他的太太是文革前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的小女儿。我的印象中援朝是一个好丈夫,甚至有点怕老婆。援朝的性格与老黄不同,比较外向,做起事来很有干劲,也能吃苦,例如他学英文的方法是把整部字典背下来。
1985年从美国回北京探亲又见到了援朝,那时他已经分在了人民银行,改名叫李若谷,可我还是更习惯叫他援朝,后来他作为中国驻世界银行的首席代表派驻纽约,我那时在匹茨堡大学教书,我们在电话上聊过几次,回去听说他已经成了人民银行的行长助理,再后来听说他做了进出口银行的行长。
3.收获
1970年代末,中国开始恢复跳交际舞,但是我们这些文革中长大的人,还不太习惯与异性近距离接触,更何况是手拉着手,肩靠着肩。我们班先是在宿舍中练习,快3、慢3、快4、慢4、探戈,后来还有“贴面舞”,风靡一时。那时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是潘琪,在班里是年龄最小的同学之一,刚开始跳舞时,他的抵触情绪非常大,从他住的房间出来,必须要经过我们跳舞的房间,我记得他每次都低着头,快步地走出屋子,丝毫不被我们的热闹场面所打动。
到我们临毕业时,交际舞已经普及,学校每周都在学5食堂举办舞会,潘琪不知什么时候居然成了舞星,逢场必到,还在舞会上认识了他的女朋友,一天晚上舞会结束,有人看到他和女朋友站在大马路中间接吻,成了那天晚上宿舍里同学们热议的话题,谁也没有想到他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会有如此大的飞跃。
那时我们班去美国留学的除了赵全胜,还有我和史天健,我们俩都是1982年毕业后出国的,后来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我在芝加哥大学,虽然在不同的学校,但我们的研究很相似,都是比较政治学,都是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中国政治,这在美国当时是很少见的,那时研究中国的主流都是偏重历史、哲学、文化。
我们毕业后,他先在爱荷华大学,我在匹茨堡大学,后来他到杜克大学,我又转到了爱荷华大学,我们经常在学术会议上见面,我们的关系可以说是又合作又竞争,因为我们的背景很像,搞的东西也很像,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他后来英年早逝。
2010年,天健不幸因免疫系统疾病突然离世,天健生前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在文革中当过卡车司机,还干过外科医生,在哥大念书时还在纽约开过出租车,卖过电话卡,他走时才58岁。没有了天健的激励,我反而觉得孤独了不少,失去了动力,不夸张地说,天健是中国政治定量研究的顶尖学者,他的著作引用量很大。
那时候我们班有12个女生,毕业后大都出了国,其中俞健年龄最大,无论是容貌还是学习都非常出色,颇受男生的注意,后来她到美国读书,毕业后结婚生了两个混血儿子,很可爱,只可惜她后来患癌症去世了,才40几岁。
另一个在美国的女生是郭津德,她在美国读了一个MBA学位,后来长期掌管麦克阿瑟基金会的投资项目,手中控制着几十亿美元的资产,收入自然不菲,但她生活极为简朴,从不张扬,在美国三十几年,不买车不买房,但对周围的朋友和同事却慷慨解囊,一个朋友自己盖房子盖了一半没钱了,她就帮人家把剩下的钱给付了,另一个朋友买了房子却付不起月供了,她就帮人家付,她的秘书是单亲家庭,生活很困难,她也无偿地提供金钱帮助。
郭津德对同学的情谊也很深,她是我们班唯一个参加了在美国去世的两位同学史天健和俞健追悼会的人,我常和她开玩笑说我得走在她前面,这样她说不定也会去我的追悼会。
我们班还有一个去了法国的女生叫茅青,在法国之声的中文部工作了多年,我的一个记者朋友听了她的节目说,她的声音很好听,也很专业。茅青为人也非常低调,上学时只知道她出身名门,具体的细节她从来没有说过,直到后来我看了她写的那本《我们家的那些人和事儿》之后,才知道她们茅家都是名人,光我认得出名字的就有茅以升、茅以新、茅于航、茅于轼等等。
大学毕业后,来到美国才发现,在学术界最基本的生存技巧之一就是写论文,而一篇好的论文都离不开历史背景,事件的经过、原因和意义,用今天的话说,一篇好的论文应当具备清晰的逻辑思路、客观中立的立场、充足的证据、敏锐的分析问题能力、鲜明的观点,以及所研究问题的重要性所在,而这些要素,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就已经接触到了。现在回想起来,北大4年的本科教育,为自己后来的学术生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尽管当时不觉得,还整天抱怨。
其中让我觉得受益最大的是对分析问题能力的训练,当时老师总是强调让学生一定要记住事件产生的不同原因和后果,哪怕是死记硬背,其实就是在锻炼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如果碰到一件事或看到一种观点,就要强迫自己想出几个原因或几个看问题的不同角度,其实就是在逼着自己去思考,这样时间长了,就会锻炼出一种自觉思考和分析问题的习惯,这在学术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至今在美国上课时,我总是要求学生至少要从两个角度看问题,以此来强迫他们思考,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毕业30年后,我有机会到东南亚旅行,才发现我们当年在北大77级本科教育所受训练的意义和重要性。我看到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有多大,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华人都是听着中国的华语电台长大的,他们对中国的政治宣传非常能听得进去,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向东”(心向毛泽东)、“向京”(心向北京)等等。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初学的实际上是如何在亚非拉地区发动革命和政变,如何推翻敌对势力,如何扶持亲中、亲共政权,无奈当时在改革开放初期,觉得这一套已经过时了。
后来到了美国,看到美国政府比中国做的有过之而无不及,整天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是美国如何颠覆其他国家的敌对势力,如何通过各种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手段扶持自己的傀儡政权,如何向其他国家灌输自己的价值观。随着中国国力的加强,中国和美国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争夺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变得越来越激烈,也让我越来越觉得过去学的有关革命与政变的理论与实践不光没有过时,反而有很强的实用性和现实意义。
原载IPP评论微信公号,版权事务请与编辑联络

矿山建设网公众号
矿山界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