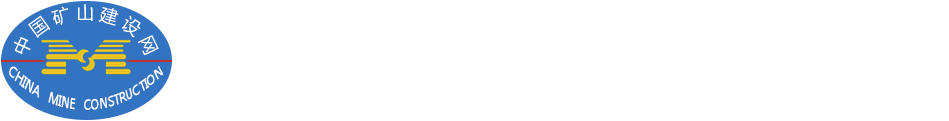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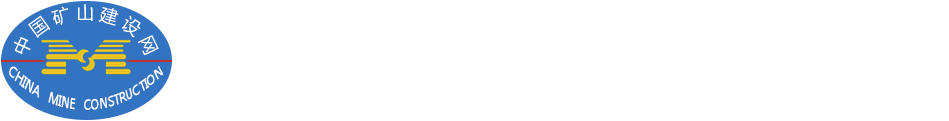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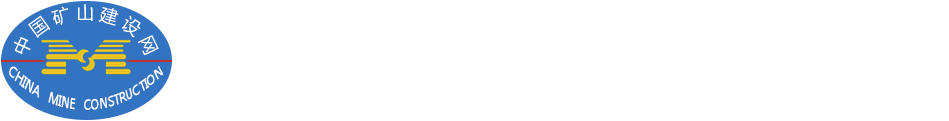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李秉铎,197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物理系,1980年再次毕业于四川大学物理系进修班(回炉班)。先后在贵州印江县粮油加工厂、印江县中学、贵阳地质一中工作。1990年调回重庆,先后在蜀都中学、重庆十八中学任教,中学高级教师。2006年在重庆十八中学退休。
原题
县中学往事
作者:李秉铎
回忆是一条感情的丝线,将随风而去的往事一件件寻觅回来,串联在一起,在退休的生活中慢慢缅怀。
一、走进县中学
1975年10月我和爱人敖艾莉一起调到贵州印江县中学任教,我教初三物理及电工学,艾莉教初二物理
印江中学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这里就有了“龙津书院”。之后几经更名,至今已有300多年的演变史。
校园内,一塔一书院远近闻名。

文昌阁
“一塔”指文昌阁,建于明嘉靖十年(1531年),寓文运昌盛之意。塔高38.72米,七层四方六棱八角攒尖顶。文昌阁属省级重点保护文物,被看作印江文明的发祥地和印江中学的象征。

依仁书院
“一书院”指清初由“龙津书院”更名而至今尚存的依仁书院。该书院是历史上印江文人主要集聚地和传道讲学的主要场所。历年来由此间走出的文人墨客不计其数。在依仁书院的办学基础上,于1940年建成新型的学校——印江县中学。
县中学是县城里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单位,当时外地分来的毕业生占很大比例,有复旦、华东师大、上海外语学院、武汉大学、暨南大学等重点大学毕业生。可谓人才济济,藏龙卧虎。

全家在柳家院子合影
我们住的宿舍叫“柳家院子”,有点象北京的四合院,进了院子的大门有一个青石板铺的院坝,也就是天井。正对大门的高大的殿堂(以前的祠堂),现隔成若干小间作各家的厨房,还有一大间作学校教职工食堂。两边是两层楼的木板房,住了十来家老师。我们住楼下,有两间木板房,房屋空间不高,我伸手可以摸到天花板。

严寅亮雕像
家刚一安定,年级组长就上门登记我是否有收音机,能收几个波段,并告诫不要收听境外敌台。然后办公室秘书给我们交待一项政治任务:监视隔壁邻居“历史反革命”严仔肩,有什么情况要及时汇报。
这个严仔肩是原县中学校长,省政协委员。其祖父严寅亮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1888年北京颐和园建成,慈禧太后下诏所有大臣为颐和园题额,但无一副书写能令慈禧中意,征选园额的诏书便一直高悬紫禁城。严寅亮赴京应考,名落孙山,落魄在京西一家客店,卖文糊口。店主人见严怀才不遇,十分惋惜。劝严写下“颐和园”三个字,并代他去应诏投递。这三个字遒劲有力,银划铁钩,令朝野震惊,被慈禧选中。并赐以龙纹饰边的“宸赏”玉章一枚。严从此以后,逢山留翰,名噪海内。朝野人士求墨宝者,络绎不绝,凡得其墨迹者,无不视若珍宝。(印江县是书法之乡,除严寅亮之外,还出过著名书法家王峙苍、魏敦全、魏宇平等,魏宇平现居重庆,曾为重庆书法协会副主席,重庆诗词学会会长)
后来我在学校的一次批斗会上看到批斗严仔肩,两个高大的学生一人抓住严仔肩的一只胳臂,像提一只鸡一样,严仔肩脚不沾地就被揪到主席台上。对一个已六十多岁的瘦小老头还采取这种暴行,引起我的同情心,加上头脑中阶级斗争这根弦本来就绷得不紧,不愿意去当一个告密者。所以和严仔肩住了两年邻居,一次也没有去汇报他的情况。我和严仔肩的儿子都在集邮,有时还在一起交流一下,互换邮票,两家相处得很好。
严仔肩平反后,对我还颇为感激,引为知已。我后来调到贵阳工作,严还写信给省图书馆及博物馆的熟人,嘱咐他们在我去借阅图书时给与方便。我庆幸自己在那个阶级斗争重于一切的年代,没有去充当一个“潜伏者”“告密者”,做出令人后悔之事。
初为人师,加上中学的东西已丢了多年,为了不误人子弟,一方面,我和艾莉备课非常认真,常常看书,写教案到深夜。另一方面,在教学过程中很快发现多数学生根本不学,因为那时未恢复高考制度,学生缺乏学习动力,上课纪律很差,因而课堂上要花很大的精力来管纪律。有一位女老师上课,班上两学生打架,在地上打滚,一直滚到讲台边。这位女教师没有办法,只好从学生身上跨过,飞奔到校长办公室“报警”。
一天正在上课,一个学生在下面和别人吵闹,说怪话。我干涉了两次都不起作用,终于忍不住冒起火来,要请这位学生出教室反省。哪知这位学生特别犟,紧紧抱住课桌耍赖。我勃然大怒,拿出我在打米厂扛200多斤重麻袋的功夫,“力拔山兮,气盖世”,一个旱地拔葱,连人带课桌一下子就扛上了肩。全班学生惊呆,顿时鸦雀无声。这位顽皮学生悬在空中,挣扎了几下,见没有用,只好投降告饶:“老师放我下来,我自己出去。”以后几天上课,这位学生都埋着头不敢看我。这也使我反思:这样对待学生太简单粗暴,有点以强凌弱,会伤害学生的自尊心,以后要有耐心,注意方式方法。
多年后,这位学生也当了老师,见了我还很不好意思。我问他是否因当年的事记恨我,他说一点也不记恨,是自己太调皮了。不过那次确实把他吓坏了。
这惊天一扛竟成了经典。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老同事见面,还拿这件事来笑话我。
二、开门办学
那个时代的教育正时兴开门办学。学校专门在操场放映当时很有影响的两部电影:《决裂》和《春苗》。《决裂》是描写江西共大松山分校开门办学,招收有实践经验的青年,甚至凭手上的几个硬茧招收大学生。批判教授上课时脱离实际,讲什么马尾巴功能。《春苗》是歌颂农村赤脚医生的影片。
高一年级有六位同学联名给学校党支部写了一封信,指出学校的开门办学只是形式上的开门,仍然是黑板上开机器、种庄稼、认化肥,学了一学期电工,连电灯都不会安装,有点象《决裂》所批判的那种脱离实际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学校组织各班讨论这封信,并决定进一步开门办学,开各种专业课,走出课堂,走出校门办学。如物理教师开设电工课,农机课(教开拖拉机),生物教师开设红医课(学医疗卫生知识)。这给老师们很大的压力,如我和艾莉就抽时间去学开拖拉机(学校有一台手扶式拖拉机),不然自己都不会开,如何教学生。
我教的电工课要尽量开门。我采取的措施是:一是带学生外出参观。我带学生到朗溪区犀牛洞水电站参观,请电站的技术员作讲解;到县广播站参观;到机械厂参观,请电工师傅讲交流互感器,磁力启动器的作用,如何接线。二是外出实习。我打听到电厂准备给新建好的外贸站安装电灯,就和电厂联系,带学生去实习。电厂的几位师傅很热情,耐心讲解,不仅让学生亲手去安装电灯,还教学生安装电度表。一连实习了两天,学生们觉得还是有所收获。但这一开门也也产生了问题:一是我带一个班的学生去参观和实习,其他班的课就上不到了,甚至有的班开学一个月才上一节物理课。二是为了学生学技术,影响安装的进度和质量,使实习单位有可能产生意见。
那时理化生是一个教研组,组内有一个教生物的的老师吴兴隆,他开设了一个“红医班”,带着学生学医,他自己也对学医有浓厚的兴趣。我有一段时间由于长期紧张工作,休息不好,患了神经性皮炎。吴老师用一个小竹块上面插上几颗大头针做成“梅花针”,然后敲打我的患处,直到出血为止。经过一段时间我的 皮炎竟医好了。我的女儿有一段时间便秘,三四天都不解大便,到县医院看病,也未解决问题,造成我和艾莉思想上极大的负担。吴老师建议服用维生素B1,增加肠道蠕动。我们试了一下,药到病除,马上就好了。还有更神奇的事:一位老师的爱人中风瘫痪,吴老师居然用扎针灸的方法使她重新站立起来,并可以行走。
和同事在文昌阁前合影左一为作者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的“开门办学”虽然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影响了各学科基础知识的系统学习,把当时的老师们折腾得够呛。但老师们在其中还是取得一些成绩,展现了知识分子的敬业精神和聪明才智。吴老师也住柳家院子,一来二往我们成了朋友。有时晚上我和他在宿舍里喝一点小酒,炒一小盘花生米作下酒菜。1978年我回四川大学进修两年,只有艾莉在家,这位老夫子遵循封建礼教,两年内没再进我家家门。后来他调回贵阳,临走时我还给他写了一首小诗作为纪念。现在我只记得其中两句:“煮酒还有花生米,谈笑风生多壮举。”
三、篮球联赛
在那个不重视读书的年代,学校体育活动却开展得很活跃。经常开展田径赛,各类球赛,记忆最深的是篮球赛。
教师篮球赛以年级组进行,另外还有行政组。因高中部班级少(那时高中是两年制),所以高中部组成高中组,各组以高中组和初三组最强。高中组是学校的老冠军队,而初三组是后起之秀。我所在的初三组有两个主力,一是吴兴隆老师,他身高1.78m,是个优秀的中锋,另一个是雷富强老师,是满场跑的控球后卫。
两个组第一次相遇,结果我们大胜高中组,赢了十几分。这一场球我发挥得很好,因对方注意力都集中在吴、雷二位身上,他们成了防范的主要对象。这使我得到了很多投篮的机会,而我的投篮一贯较准,特别是在篮圈两侧的擦板球,可以说十拿九稳。这一次我成了取胜的一匹黑马。
最后这两个组进入了决赛,双方都铆足了劲要战胜对方。高中组开了多次准备会,商量打法。我们也开了几次准备会,并由一位热心的女老师给每位运动员赶制了白色运动短裤,上身则统一购买蓝色背心。
决赛在五月初的一个晚上,在学校灯光球场进行。那天全校教职工,部分学生及学校附近的居民都前往观看。球场四周人群簇捅,不时响起双方啦啦队的歌声、口号声,场面十分热闹。球赛一开始我们就处于下风,我被看死了,得不到投篮的机会。雷老师上半场就犯了四次规,产生了情绪,发挥得也不正常。最多时我们输了6个球。下半场我们仍然一直落后,形势不利。但我们一直不放弃,把球尽量传给吴、雷两人,让他们进球,慢慢把分追上来,最后5分钟时终于打平,接着反超,最后赢了三个球。
这场球赛我们主要赢在年轻体力好,输球后仍能团结一致,坚持到底不放弃。高中组这场球在战术的运用,技术的发挥上都比我们强,但他们普遍年龄比我们大几岁,体力要差一些,所以最后被我们追上并反超。赛后我们准备了酒菜,把全组老师请来,在吴兴隆的宿舍里欢聚一堂,庆祝胜利。那场激烈精彩的球赛,及胜利后全组老师喜洋洋的表情,至今仍历历在目。
四、校办农场之殇
县中学张校长四十多岁,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精壮汉子。他迫切想在教育革命中有所作为,先后去参观了全国教育革命典型江西共大和朝阳农学院。决心大干一场,办个颇具规模的校办农场。

我和艾莉在印江边
农场场址选在离校五六里的甲山镇。印江河水在这里拐了一个湾,形成一个河套,校长决定在河坝筑堤,让河水改道走直线,把整个河套都改造成良田。这个工程很宏伟,工作量也很大。
1975年底校办农场上马。先是造舆论,在工地上开展赛诗会。我记得写了一首诗:
农场和北京紧相连
校办农场有多宽?
块块田土望不到边;
站在河滩放眼望,
金光大道通向前;
一头通向北京城,
一头连着井冈山;
毛主席指引光辉路,
教育革命迈大步。
那时候的我还是挺革命的,也挺有革命干劲。
当时学校的一对年轻老师结婚,学校送的一套毛选,一把锄头,一个草帽,叫革命化的婚礼。
1976年寒假,从1月27日到2月15日,除春节放假一天外,全部用于政治学习,星期天都不休息,叫做过革命化的春节。县中学则利用这段时间组织老师到校办农场劳动。为了完成劳动任务,甚至还推迟第二学期开学时间。
校办农场的劳动很艰巨,我参加专业队,在河边的山坡上用钢钎打炮眼,放炮,撬石头。七八百斤重,一二千斤重的石头轰隆隆地发出巨响从山上滚下,伴随着一阵阵欢呼声,热闹极了。劳动第二天我就受了伤,在用钢钎撬一块大石头时,石头未滚下山,反而回下来把我手中的钢钎弹飞,钢钎从我下颏下面飞过,划了一条长长的口子,那儿正是柔软的地方立即象又张开了一张嘴巴,鲜血顺脖子流下。在工地上只有由校医上了药,包扎了一下,我在草地上休息了个把钟头,就又参加了劳动。那时也不知道去缝几针,所以至今都留下一道疤痕。
第二步是抬石头筑堤。有四人抬的石头,八人抬的石头,最大的一礅石头用了十个人才抬动。由于几年体力劳动的锻炼,所以我总是争着抬重的石头,很快就被称为“压不垮的铁肩膀”。连一些老教师都不再称呼我为“小李”,而尊称为“老李”了。但很快我就遭受了挫折。一次八人抬一礅大石头,我走在最后,上坡时,大石头突然后滑,我只感到腰一胀,有如泰山压顶,一股巨大的力量压下来,这是我从未承受过的重量,我的双脚立即象钉在了地上,一步也挪不开了。我立即喊道:“快!我不行了!”有好几个老师上来帮我支持住扛子,我才从重负下脱了身。我们教研组的组长运气就没有我这样好了,他在抬石头时不堪重负,一下子被扛子压倒,嘴正啃在石头上,门牙被磕掉两颗。
劳动虽然艰苦,但大家仍比较愉快。一是校长身先士卒,处处带头干重活,不搞特殊,令人信服。二是伙食开得好,每天开一元钱伙食,一日三餐,晚上有酒有肉。三是担任班主任的老师用不着去管理几十个学生,只要管好自己就行了,感受到“无官一身轻”。
劳动休息时,老师们在一起天南海北地吹牛。我记得一个老师讲流传的故事“十二号房间”,几天都未讲完。男老师们常常避开女同胞单独聚会,这样可以放肆地讲些只能供男人们听的荤龙门阵。
艾莉因为生小孩未参加农场劳动。期末改完学生试卷后就请假生小孩。到第二学期开学,离满月还差几天,就应校长的要求提前上班了。前后没因生小孩耽误一天上课。那个时代的人真是太听话了,太能吃苦了,因而也特别容易领导。
开学后学生也参加了劳动,各年级轮流上阵,星期天也不休息。河堤修好后,就大规模地挑土造田了。在河堤上人工填土造成几十亩田土,并种上秧苗,洋芋苗。看着一片平整的土地,长满绿油油的庄稼。大家想着秋后的丰收,充满劳动的喜悦。
到了五月中旬,接连几天大雨,河水暴涨,我们修的河堤不够高,农场进了水,冲走了不少洋芋、秧苗。大家过不了河,只能在河边观看对岸农场的灾情,心里干着急。又过了几天,大家还未回过神来,又是一场倾盆大雨,天黑沉沉的,象要垮下来一样,大雨从黎明开始,下了一整天。河水象脱疆的野马冲垮了堤坝,农场成了一片汪洋。事后我们见到一片狼籍的农场,辛辛苦苦抬的大石头被冲得七零八落。看到几个月流血流汗换来的劳动成果毁于一旦,真是欲哭无泪。我看见校长呆呆地站在一墩大石头上,他颀长的身材,圆圆的脑袋,象一个倒立的惊叹号。在大自然的强大力量面前,我们的努力显得那么渺小,不堪一击。我们的农场梦也就此破灭了。

现印中教学楼
后记
记得在大学学《量子力学》,这是一门艰深难学的课程,授课的是一位女教师,每次上课都照着笔记本念,缺乏自己的发挥和见解。我们私下议论:哪次偷掉她的笔记本,看她怎么上课。我们向她反映,这门课很难学,上完课我们还是懵懵懂懂的(言外之意是考试时高抬贵手,出题简单一点)。这位女老师坦诚地告诉大家:她是1958年的大学生,那个年代大炼钢铁,大跃进,教育革命,实在没有学到多少专业知识,现在只有尽力而为,请大家谅解。

回忆教育部门几十年的教育改革历史,就是一部折腾史。总有一种力量让你不能静下来正常生活,正常工作。总要让你卷入变化莫测的政治风浪之中,去跟天斗,跟地斗,跟人斗,斗到天怒人怨。正如一位科学家所说:那些年代我们做了许多令人可笑的事。
1977年,一声春雷,高考恢复了。存在决定意识,课堂纪律变好了,老师也受到人们尊重了。那时师生关系还是一种“原生态”的朴实状态。老师假期给学生补课,完全是尽义务,是不收费的。过年过节,家长争着请老师到家作客,特别是有点名气的老师若能赴宴,会使家长感到很有面子。我记得一个学生考取了大学,他是那个寨子里出的第一个大学生。他的父亲居然用洗脸盆装了一盆米送给我,说没有东西送,只有送点米表示感谢。
教育又回到了正常的轨道,在以后二十多年的教书生涯中我没有再从事过繁重的体力劳动了。为了不断提高升学率,又陷入一种繁忙的脑力劳动之中。

现在的印江中学校门
2009年5月于重庆
来源:新三届
责编:龙志阳 | 编辑:龙志阳